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从摩根大通到贝莱德(一)
前言
1: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美国金融的兴衰
金融化的新图景
重新思考金融与公司
2:古典金融资本与现代国家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
从银行资本到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与竞争
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与危机
3:管理主义与新政国家
重塑资本主义金融
新工业秩序
阶级斗争与管理主义危机
4:新自由主义与金融霸权
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
资产积累与市场金融
金融化与威权国家主义
2008年危机与衰落问题
5:新金融资本与风险状态
危机管理与风险状态
三巨头的崛起
新金融资本
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和金融资本
6:危机、矛盾和可能性
市场金融的国家化
金融资本的宏观经济政策
普遍所有权的虚假承诺
金融民主化
1: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变化。随着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危机管理努力将国家权力更深入地带入金融体系的核心,连续几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促进了企业所有权前所未有的集中和集中在一小群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在危机之后,这些公司——贝莱德、先锋和道富——取代了银行,成为当代金融领域最强大的机构,积累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范围的所有权。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了一个庞大网络的中心节点,该网络几乎囊括了每个经济部门的所有主要公司。
这相当于企业权力的历史性转变。自新政以来,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一直是公司组织形式的一个核心特征:拥有公司的人(股东)在形式上不同于控制公司的人。在危机前的几十年里,市场调节了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股东可以通过出售表现不佳的公司的股票来“退出”。但随着金融危机后三大巨头的崛起,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作为“被动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只能进行交易,以反映他们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或纳斯达克等股指上所持公司不断变化的头寸。由于无法随意抛售股票,他们转向了更直接的控制工业公司的手段。
自镀金时代以来,这种对工业企业的金融影响从未见过,当时摩根大通等巨头主导了美国资本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权的集中受到一个基本权衡的限制:投资者可以拥有大量公司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也可以拥有少数公司中的很大一部分。换句话说,随着多样化程度的提高,许多公司的股票持有量被稀释,限制了投资者对任何特定公司的控制权。因此,投资者可以积累足够的股份,对相对较少的公司施加实质性的权力。自2008年以来,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崛起扭转了这一局面:三巨头几乎成为了所有最大、最重要公司的最大股东。
如今,三巨头共同成为美国经济中占总市值近90%的公司的最大或第二大股东。这包括标普500指数中98%的公司,该指数追踪美国最大的公司,三巨头平均每家公司拥有20%以上的股份。同样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危机后这种集中发生的速度。从2004年到2009年,道富银行的管理资产(AUM)增长了41%,而先锋集团的资产增长了78%。然而,贝莱德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独特意义反映在其资产管理规模在这些年里爆炸式增长了几乎不可信的879%,到2009年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
这一转变的速度和规模预示着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前所未有的所有权集中,以及围绕少数金融公司的公司控制权集中。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现在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高度活跃、直接和强大的作用,它们对美国经济中几乎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是如此。他们已经成为“普遍所有者”,管理着美国的全部社会资本。
美国金融的兴衰
2008年后建立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公司之间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和工业资本融合形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鲁道夫·希夫丁于1910年将其称为“金融资本”。尽管该术语被广泛滥用,但金融资本并不仅仅是指金融资本,更不用说银行资本了。相反,金融资本是通过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而出现的,是通过它们的结合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一种扬弃了原始工业和金融形式的综合(黑格尔的术语)。通过这一过程,金融机构在工业企业的管理中发挥了积极和直接的作用。通过塑造其控制的公司的战略方向和组织结构,金融家旨在以股票价格、股息和其他利息支付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货币资本的回报。
金融资本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来说,金融化是指货币资本——或货币预付然后带息返还的循环——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中取得更大主导地位的过程。正如人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货币资本的扩张是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反映在“股东价值”原则中,即公司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给予投资者更大的回报。目前形式的金融资本代表了一种更加集中的金融化形式,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无论是更广泛的金融化趋势还是金融资本的出现,都没有像人们经常声称的那样表明资本主义的衰落或工业的空心化。相反,金融化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提高生产率和剥削劳动力。
此外,与许多将金融化描述为与前新自由主义、非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突然决裂的说法相反,我们认为金融化的根源在于战后时期,当时它是一系列国家努力在金融和工业之间实现“水密”分离的结果。追溯20世纪后三分之二到21世纪前二十年金融权力的崛起,从摩根大通帝国的崩溃到贝莱德的崛起,我们呈现了一部挑战大众账户的美国金融史。在我们勾勒的弧线中,金融化的历史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古典金融资本、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金融资本。这些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包括金融权力的衰落,然后是渐进、不平衡和矛盾的重建。每个阶段都以国家、企业和阶级权力的特定组织形式为特征,过渡不是以尖锐的“断裂”为标志,而是以连续性和变化为标志。
希夫丁的金融资本理论源于他对19世纪末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然而,他的分析在美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这个经典的金融资本时期(1880-1929),投资银行通过合并小企业组建了大公司。这些银行的权力取决于它们对公司股票的所有权和发放信贷的能力。随着投资银行向工业企业发放大量贷款,两者的利益变得紧密交织:工业企业依赖信贷,而投资银行则寻求确保贷款得到偿还,因此他们监控企业运营以保护其投资。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地位确保了他们对公司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在董事会中获得席位,并为他们控制的公司建立“连锁董事会”。
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股权日益分散,这些金融资本网络变得更加松散。一个新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对工业公司行使着越来越自主的控制权,银行沦为一个纯粹的支持部分。1929年股市崩盘后颁布的法规使管理时期(1930-1979年)神圣化,该法规正式将银行与工业公司的治理分开,并使“内部”公司经理成为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大集团的持股,这些经理可以控制工业企业,而不会面临投资者的一致挑战。然而,与此同时,将银行与工业公司分离导致后者将一系列“金融”职能内部化,发展了独立筹集和发放资金的广泛能力。因此,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起源于战后“黄金时代”的核心。
这一时期工业企业的霸权得到了新政国家的支持,新政国家有三个关键属性。首先是它对合法性的关注。新政改革,如工会权利和社会保障,旨在消除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并将工人纳入了管理霸权的结构。其次,这些改革导致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巨大扩张,而国家财政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税收提供资金的。因此,新政州是一个税收州,其再分配计划导致收入不平等水平降低。这也是由于基本上不关心政治的工会在集体谈判中取得了成功。最后,产业霸权得到了家族工业复合体的支持,家族工业复合体将最具活力的公司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导致所谓的跨国公司(MNCs)的巨大增长和多样化,并促进了多部门企业集团形式的公司组织的发展。
随着战后繁荣在20世纪60年代末放缓,工会工资斗争日益挤压企业利润,导致合法性和积累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工会权利和新政计划现在对积累构成了障碍。这一问题通过新自由主义威权国家的形成得到了解决,该国家通过前所未有的利率飙升和新一轮全球化来约束劳工。随着国家权力集中在不受民主压力影响的机构,特别是美联储,选举和政党变得更加不重要。这种威权主义结构因新自由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缺陷的国家而得到加强。随着减税以恢复企业利润,国家项目越来越多地通过债务融资,加强了财政对国家预算的约束。这也加剧了不平等。富人现在不再为再分配计划纳税,而是将国家资金借给他们偿还利息。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1980-2008),工业霸权被一种新的金融力量所取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为企业在国际化生产网络中流通价值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金融霸权也得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由专业基金经理管理的工人养老基金激增的支持。在这些新的“机构投资者”中发生了公司股票的集中和集中浪潮,这些投资者对工业公司拥有重大权力。然而,这种形式的金融权力与经典金融资本截然不同。与其说是单个银行直接控制企业网络,不如说是竞争性金融机构的集群施加了广泛的结构纪律。
然而,金融霸权并不是由外部投资者压力强加的,而是最初在工业企业内部出现的,这是战后几十年对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适应性反应。事实上,这是多部门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一个内在方面。大公司不再围绕一个业务组织,而是由许多不同的业务组成,这些业务往往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关系。此外,这些行动的范围越来越国际化。这带来的挑战导致企业集团将业务部门的运营管理分散化,即使投资权集中在高层管理人员手中。这些所谓的“总经理”并不管理具体的生产过程,而是管理货币资本本身;到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已经成为金融资本家,坐在金融和工业的纽带上。
随着工业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发展,其财务部门和职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公司财务主管转变为首席财务官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席财务官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得力助手,负责建立“投资者期望”并进行必要的内部重组以满足这些期望。工业企业的财务能力也在扩大,因为它们试图通过从事衍生品交易来管理全球化的风险。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多层子公司形式的公司组织的出现,跨国公司通过将其内部部门与外部分包商的第二层整合来组织生产,形成高度灵活和有竞争力的全球网络。苹果对富士康的依赖只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新金融资本是在2008年危机后形成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股东资本主义的分散金融权力集中在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监管机构试图通过精心策划银行合并来增强系统稳定性。尘埃落定后,只有四家大型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主导了该行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干预导致人们从银行转向一群资产管理公司,即贝莱德、道富和先锋。随着风险状态的形成大大降低了股票的风险,资产管理公司为大量资金涌入这些资产提供了便利。将储蓄引入股票进一步降低了风险,导致股价持续上涨,资产管理公司的所有权也同样持续集中。
资产管理公司集中所有权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其投资组合的管理委托给这些公司。通过汇集这些基金中已经积累的大量资本,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集中了金融权力,获得了自摩根大通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经济主导地位。这得益于向被动管理的历史性转变。与主动管理不同,在主动管理中,高薪基金经理通过“击败市场”寻求回报最大化,被动基金无限期持有股票,交易只是为了跟踪特定指数的走势,这使他们能够提供大幅降低的管理费,特别是在股价上涨的情况下,获得高回报。但这些被动投资者是非常积极的所有者。由于他们不能通过简单的股票交易来约束工业企业,他们追求了金融资本特有的更直接的影响方法。
如果资产管理公司的崛起是美国资本主义组织历史性转变的一部分,那么这尤其围绕着贝莱德的卓越地位。到2022年,贝莱德管理的资产已达到10万亿美元。如果将其通过Aladdin软件平台间接管理的资产包括在内,这个数字接近25万亿美元。贝莱德现在是几乎所有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主要所有者之一。资本的集中程度从未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它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其管理的资产规模上,还体现在其与国家的特殊联系上。乔治·W·布什在任期内选择高盛的汉克·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而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都考虑过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担任该职位。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也是贝莱德的高管。所有这些都表明,一部分新的金融资本家的力量正在增长。
金融化的新图景
本书对金融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与进步政策平台和批判性学术中的分析明显不同。事实上,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特别是在2008年危机以来的几年里,金融是“实体”工业经济的腐蚀性和寄生性力量。新自由主义的许多弊端也是如此,从经济危机到社会不平等,通常被归因于“金融化”。虽然进步派担心,如果没有监管来控制金融权力,美国的繁荣和竞争力将会减弱,但马克思主义者则通常将金融化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症状和美国帝国衰落的预兆。这些想法激发了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之间的政治辩论,以及从希拉里·克林顿到杰里米·科宾等政治人物的政纲。
许多观察家追随Giovanni Arrighi的观点,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增长和衰退周期中不可避免的阶段。在这种观点中,霸权国家的衰落与金融的增长密切相关。然而,Arrighi淡化了金融在资本主义早期增长和活力中的核心作用。投资银行是19世纪现代公司组织的关键参与者,正如在目前,金融仍然是当前多层子公司形式的公司组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融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构成了通过国际化生产体系实现价值流通的基础设施。金融的日益突出并不是指美国帝国的衰落,而是强调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和格雷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等进步人士认为,金融的兴起导致了生产的“空洞化”,这与衰退的故事相呼应。他们认为,金融业关心的不是投资于长期增长和繁荣,而是“快速赚钱”。因此,金融业的崛起给工业企业带来了“短期主义”,导致他们放弃了对战后支撑“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好工作”的投资,以及美国企业保持全球领导地位所必需的研发。相反,企业将资金转移到“非生产性”金融服务上,并中饱私囊。高管们获得股票期权的补偿只会增强他们参与这种功能失调的策略的动机,导致他们通过股票回购来抬高股价,以获得意外之财。
然而,战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原因不是公司经理的仁慈或远见,而是阶级力量的平衡,特别是工会赢得工资增长的能力。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这些分配交易得到了战后繁荣的独特环境以及自由资本流动出现之前的世界贸易结构的支持。导致不平等加剧和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社会计划倒退的原因不是金融的兴起,而是资本主义无法支持这些妥协。随着战后繁荣的结束,工会的工资斗争挤压了利润,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危机,这场危机只有在劳动力失败和大量低薪劳动力通过全球化被剥削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因此,金融化是恢复盈利能力和解决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关键,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尽管这个黄金时代不如第一个“黄金时代”。
此外,将金融从根本上视为短期主义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大明星尽管在短期内没有盈利,但却吸引了大量投资。例如,优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投资者一直在展望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发展,预计这将使该公司在某个时候盈利。特斯拉也一直专注于全新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长期发展,即使它在汽车销售上亏损。尽管利润很低或根本没有利润,但投资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向亚马逊投入了大量资金,《经济学人》将其描述为“历史上对公司长期前景的最大赌注”。同样,许多行业的工业公司愿意承担新自由主义几十年来全球重组的巨大短期成本,以确保其长期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这一切都不足为奇。毕竟,为什么金融家或公司高管会有意破坏自己资产的长期价值?此外,认为支付股息或进行股票回购必须以牺牲新投资为代价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在低利率的背景下,投资于生产和研发与进行回购和支付股息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因为公司几乎可以免费借款。事实上,在过去四十年里,企业投资和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都有所增加,股息支付也是如此,利润也急剧上升。尽管通过回购将大量剩余现金返还给投资者,但苹果、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对研发的持续投资显然足以保持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除了对华尔街的短期主义特权表示遗憾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金融化”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深层次的——甚至是根本的——危机。对于Robert Brenner、Cédric Durand和David Harvey来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投资从制造业转移到相对盈利和快速增长的金融服务业。他们认为,这通过产生一系列投机泡沫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幻觉,而这些泡沫只是掩盖了工业盈利能力的潜在不足。法国经济学家François Chesnais将金融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与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联系起来,但他也认为,金融化是以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为特征的长期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对切斯奈来说,这场长达四十年的“全球衰退”表明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衰落。
这些观点基于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某种解释,根据该理论,许多形式的金融资本是“虚拟的”,与“真实的”工业资本是分开的。在这种观点中,金融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工业通过支付各种形式的利息(包括贷款利息以及股息和服务费)产生的部分剩余价值的被动接受者。将从公司股票到衍生品的一切都视为虚拟资本,充其量只能淡化这些金融工具在工业资本完整性中的作用;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金融视为“实体”经济的癌症,因此如果没有它,实体经济会更好。这为解释“空心化”的社会民主理论打开了大门-尽管这些理论家通常旨在证明资本主义是注定的,而不是通过抑制金融来拯救资本主义。
金融与工业并不对立。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展示的那样,它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深刻的联系。金融——无论是在非金融公司内部还是外部——都规范了剩余价值的提取,促进了竞争力,并促进了资本的国际流通和价值化。金融与工业并不对立。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展示的那样,它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深刻的联系。金融——无论是在非金融公司内部还是外部——都规范了剩余价值的提取,促进了竞争力,并促进了资本的国际流通和价值化。跨国公司能够在眨眼间在世界各地自由转移投资,这是它们构建和重组灵活、动态和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关键条件。衍生品远非仅仅是一个投机的“赌场”,尤其是对于企业管理全球化生产的风险至关重要。金融对于企业并购以及在近几十年工资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维持消费也至关重要。
激进经济学家Costas Lapavitsas避免将金融定义为独立于或反对工业,强调其在资本主义中的结构性作用。然而,在认为金融“剥削我们所有人”时,他倾向于最小化金融在价值生产中的重要和非常积极的作用。金融不仅是经济中的食利者和榨取性力量,而且对于提高生产性资本的竞争力和活力至关重要。此外,他主要从改变资产组合的角度来理解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即工业公司在金融服务上投资更多。公司更深层次的转型,即货币资本在其组织结构中变得更加突出,尚未得到探索。拉帕维察也没有充分质疑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错过了新自由主义股东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股票集中在强大的机构投资者手中,投资者对非金融公司的纪律加强,公司治理的重组反映了金融的赋权。
也许最关键的是,拉帕维察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在组织经济结构和金融政治霸权方面的核心作用。这一遗漏为罗伯特·布伦纳、迪伦·莱利以及塞德里克·杜兰德等解释铺平了道路,他们认为国家如今已被腐蚀性金融部门工具化或“俘虏”。本书提出的一个关键论点是,相反,国家在管理和构建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反映了尼科斯·普朗克萨斯所说的在监督资本主义的总体、长期系统利益方面,国家相对于特定资本主义公司和小部分的“相对自治”。正如我们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要求国家管理权力集团内不同资本部分之间的权衡和权力冲突——尽管总是在更深层次的经济矛盾和压力的背景下。
正如Leo Panitch和Sam Gindin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金融既不是对生产的挑战,也不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相反,它是美国帝国秩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使全球化成为可能。对他们来说,全球金融一体化代表了美国政府自二战以来“打造全球资本主义”项目的高潮。美国国家监管世界体系的独特帝国责任,首先是致力于确保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无论其国籍如何,从而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而不是独特的区域或国家资本主义。正如他们所示,这一点的关键基础是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尽管这意味着金融将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更加强大,但工业企业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也从中受益。
帕尼奇和金丁指出了美国国家独特的帝国角色、国家制度发展和金融兴起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这样做,他们表明全球化不是经济“法律”的自动结果,而是需要发展特定的国家能力。这导致了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国家权力集中,并使其免受民主压力的影响。这种独立性使这些机构能够灵活地干预管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受民主问责制的任意性或资本家的直接“俘虏”。因此,相对自治的国家能够代表资本行事,如果不是按照资本的要求行事的话。金融化、全球化和更专制国家的发展都是“制造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
财政一直与国家密切相关,形成了大卫·哈维所说的“国家财政关系”,即财政与国家机构的一部分“直接整合”。如果不考虑国家权力在支持和保护财政方面的核心作用,就无法理解财政;如果不考虑国家权力与经济的融合,就无法理解国家权力的结构。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认真尝试追踪美国国家经济机构的历史发展。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那样,二十世纪金融体系的演变取决于国家经济职能的不断扩大,导致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威权主义权力结构,这是当今新金融资本的基本基础。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还列举了20世纪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些重大转变,包括金融化。然而,他们往往未能将制度变革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联系起来,因此无法理解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积累的竞争性重组的,也无法理解这种重组是如何产生的——甚至认为经济集中会导致竞争力的抑制,而不是加剧。此外,这些账户中对制度的关注,而不是对价值的生产和流通的关注,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金融化是随着新自由主义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突然出现的,从而忽视了在本质上是货币经济的情况下,金融和生产之间始终存在的更深层次、更复杂的相互联系。阶级斗争的动态也是如此,这对理解历史至关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社会学家约翰·斯科特展示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机构投资者的集中如何产生了从主要由内部人士控制的管理公司到新自由主义公司的历史性转变,后者以“多元金融霸权”的形式受到更大的投资者纪律的约束。与传统金融资本中的个人投资银行直接控制公司网络不同,相互竞争的金融机构在公司董事会上建立了短暂的联盟,以对公司“内部人士”施加广泛的影响和纪律。杰拉尔德·戴维斯更进一步,声称共同基金(尤其是富达)的资产集中已经构成了一种“新金融资本”。然而,他认为,由于监管限制、利益冲突、积极互助的短期性质,这种集中的所有权并没有转化为控制。资金,以及简单的股票交易比直接活动更容易的事实。
因此,戴维斯将新的金融资本定义为“历史上独特的集中度和流动性的结合”,相当于“没有控制权的所有权”。然而,戴维斯没有预料到,被动投资基金(如贝莱德、先锋集团和道富街管理的基金)中真正惊人的股权集中将如何改变这些动态。戴维斯认为,1万亿美元的富达基金“在投资方面难以保持灵活性”,导致其转向其他业务领域。然而,仅贝莱德目前就管理着10万亿美元的资产。此外,正如戴维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富达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投资者,而这些被动基金是极其长期的。因此,他们不是通过交易而是通过直接控制来行使权力。新的金融资本和旧的一样,建立在集中和长期主义的基础上,因此首先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融合来定义。
1.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独立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
2.本文版权归属原作所有,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
您可能感兴趣
-
 Antalpha宣布战略投资Tether Gold ,拓展机构借贷产品新赛道
Antalpha宣布战略投资Tether Gold ,拓展机构借贷产品新赛道新加坡, 2025 年 5 月 27 日 —— 纳斯达克上市的金融科技平台 Antalpha Platform Holding Company(NASDAQ: ANTA)(以下简称“Antalpha”
-
 投资加密资产:判断对错的周期与风险控制
投资加密资产:判断对错的周期与风险控制在周五的文章中,有读者留言: “......对自己看好的标的长期持有......确实可以做时间的朋友收益最大化,但是有一个前提:你的选择是对的。然而,万一错了呢,人生有几个十年八年?几乎所有价值投资者
-
 Antalpha 宣布战略投资 Tether Gold ,拓展机构借贷产品新赛道
Antalpha 宣布战略投资 Tether Gold ,拓展机构借贷产品新赛道提示:本文系投稿,不代表 ChainCatcher 观点,亦不构成投资建议,请谨慎看待。纳斯达克上市的金融科技平台 Antalpha Platform Holding Company(NASDAQ:
-
 豪掷2.5亿加元,Robinhood收购WonderFi抢占加拿大加密高地
豪掷2.5亿加元,Robinhood收购WonderFi抢占加拿大加密高地原文作者:KarenZ,Foresight News5 月中旬,美国零佣金交易平台 Robinhood 宣布以 2.5 亿加元(约 1.79 亿美元)全现金收购加拿大数字资产服务商 WonderFi。
-
zkLink 社区通过将 2% ZKL 跨链至 Solana 提案,探索多链 AI 协作路径
深潮 TechFlow 消息,5 月 27 日,据 Snapshot 显示,zkLink 社区近日正式通过关于将生态基金中 2% 的 ZKL 跨链至 Solana 网络的提案。此次提案旨在支持 zkL
-
 日报 | ChainCatcher 位列港区 iOS App Store 新闻类免费榜第 7;币安将向 Alpha 积分达 204 用户发放 875 枚 PFVS 代币
日报 | ChainCatcher 位列港区 iOS App Store 新闻类免费榜第 7;币安将向 Alpha 积分达 204 用户发放 875 枚 PFVS 代币整理:Jerry,ChainCatcher重要资讯:ChainCatcher 位列港区 iOS App Store 新闻类免费榜第 7 Upbit 将上线 Sophon (SOPH) 币安公布 ELD
-
 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从摩根大通到贝莱德(三)
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从摩根大通到贝莱德(三)原文标题:《The Fall and Rise of American Finance》 原文作者:Scott M. Aquanno、Stephen Maher 原文编译:MicroMirror4:
-
 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从摩根大通到贝莱德(二)
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和重建:从摩根大通到贝莱德(二)原文标题:《The Fall and Rise of American Finance》 原文作者:Scott M. Aquanno、Stephen Maher 原文编译:MicroMirror本杰
- 成交量排行
- 币种热搜榜
 Pepe
Pepe Nexpace
Nexpace UXLINK
UXLINK OFFICIAL TRUMP
OFFICIAL TRUMP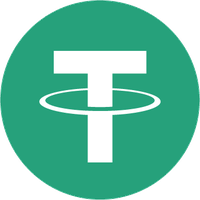 泰达币
泰达币 比特币
比特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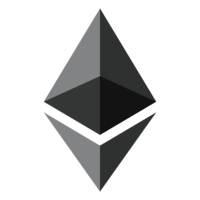 以太坊
以太坊 USD Coin
USD Coi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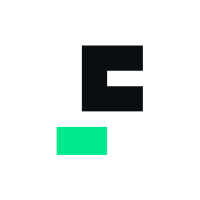 First Digital USD
First Digital USD Solana
Solana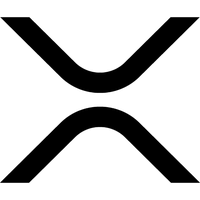 瑞波币
瑞波币 狗狗币
狗狗币 莱特币
莱特币 币安币
币安币 Sui
Sui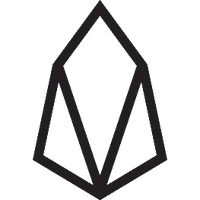 EOS
EOS FIL
FIL SHIB
SHIB ZEC
ZEC MASK
MASK UNI
UNI CAKE
CAK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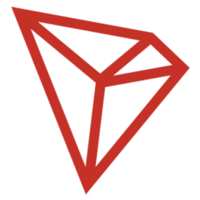 TRX
TRX DYDX
DYDX ZEN
ZEN